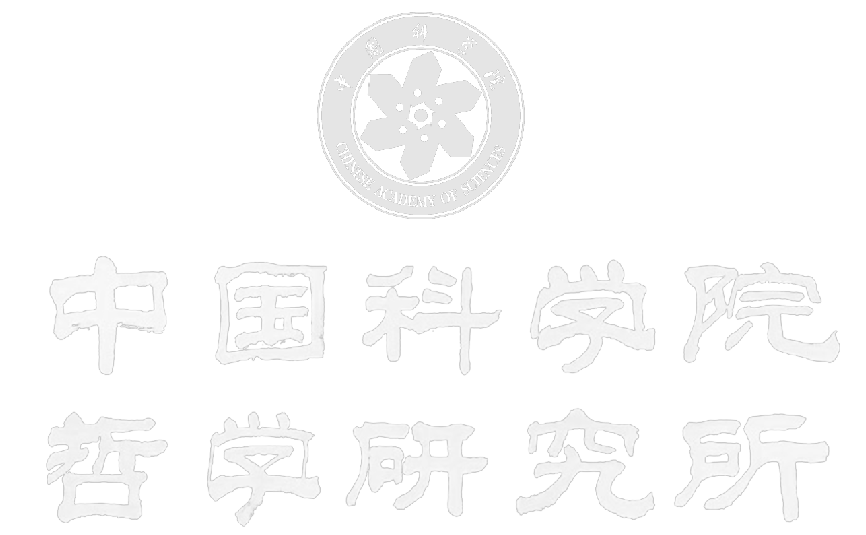编者荐语:
《中国科学报》: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中国科学院为什么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哲学研究所?
郝刘祥:中国科学院布局成立哲学所,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建立科学与哲学的新联盟,来提升中国的科技原创能力。
当代基础科学前沿直接关联着众多重大哲学问题,比如数学的基础和本性问题、量子理论中的本体论问题、复杂性科学中的突现论问题、认知科学中的心脑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于人类理解和改造世界、促进自身文明的发展,构成历史上罕见的重大挑战和革命性转变的契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国际上许多著名大学纷纷设立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机构。
当前中国科技发展正处于阶段性跨越的关键节点,同时中国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变得不是那么友好。为提升中国的科技原创能力,中国科学家就必须紧扣科技前沿中的基本问题进行开拓和创新,而不能只是在已建立的研究路径上跟踪国际上的工作。越是基础性的、开拓性的研究工作,离哲学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就越近。因此,建立科学与哲学的新型联盟,为未来的科技革命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中国就变得尤为迫切。
除此之外,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智能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要想成功应对这场挑战,同样需要建立哲学与科学的联盟。
《中国科学报》:目前国内的哲学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社会科学院下设的哲学研究所,以及综合性大学的哲学系或哲学学院,中科院哲学所的定位与它们有何不同?
郝刘祥:无论是社科院哲学所,还是北大、复旦等高校的哲学系或哲学学院,目前的学科设置都是参照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哲学二级学科分类标准,设立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和科技哲学等8个研究室或教研室。
这一分类标准,与国际上流行的哲学学科分类体系有较大出入。国际上的哲学学科分类,要么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将哲学分为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和伦理学四大部门;要么根据所研究的对象将哲学分为众多的分支学科,比如科学哲学、心灵哲学、语言哲学、数学哲学、行动哲学等。
与国际哲学界相比,国内哲学界与科学脱节的现象更为明显。按照国务院学位办的分类标准,与科学相关的分支学科只有科技哲学。而在国际上,与科学密切相关的哲学分支,除了一般科学哲学外,还有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等。特别要强调的是,一般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的是科学方法论问题,而物理学哲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物理学,更包括物理学所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自然本身。
国内哲学的这种发展现状,与科学技术在当代文明中的优势地位是明显不相称的。哲学所的定位,是用“哲学加科学”的思路取代传统的“科学的哲学”思路,以哲学和科学中的共同重大问题为研究导向,从哲学角度助力科技创新,从科技角度推动哲学发展。
《中国科学报》:立足科学与哲学的交叉融合,哲学所是如何进行学科布局的?
郝刘祥:结合当前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动态和中科院现有的研究基础,哲学所设立了逻辑学与数学哲学、物质科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认知与智能科学哲学,以及科学与价值等5个研究中心。
前4个中心,顾名思义,主要致力于开展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的研究。科学与价值中心紧扣当代生命技术和智能技术研发的伦理准则问题,结合进化论、脑科学、决策论等学科的进展,来探讨伦理的基础和道德的本质。
《中国科学报》:过去一年,哲学所建设有哪些重要进展?
郝刘祥:过去一年,哲学所在人才引进、重点项目实施和对话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都在稳步推进之中。
首先是人才招聘。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批国际招聘,第二批国际招聘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我们的目标是组建一支规模适度、固定与流动相结合、哲学家与科学家相结合的国际化研究团队,每个中心计划招聘学科带头人1名、学术骨干5名。
第二,部署重点课题、制订研究计划。目前我们已经确定选取量子理论的哲学基础问题、大脑与智能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生命技术研发中的伦理问题,作为研究所筹建初期的主要研究任务。
第三,建设面向科学家的哲学资源库。通过建立类似于“斯坦福哲学百科”那样的文献数据库或提供资源链接接口,使国内科学家能够便捷地获取所需的哲学和科学思想资源。
第四,搭建科学家与哲学家对话交流的平台。去年底我们与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共同举办了“互联网背后的哲学思考”研讨会;今年5月我们与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共同启动了“生命科学与哲学”系列学术沙龙;目前我们正在举办国际科学与哲学线上系列讲座。
《中国科学报》:按照今天人们的一般理解,哲学与科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哲学和科学在历史上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郝刘祥: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知道现代科学是如何诞生的。在此,我想引述当代著名科学史家弗洛里斯·科恩的研究成果。我认为他的见解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合理的答案。
科恩说,在17世纪科学革命到来之前,人们有三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第一种是哲学的方式。哲学家认识世界会先假定一些最基本的原则,然后利用逻辑演绎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典型代表就是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第二种是数学的方式。数学家抹去性质差异,保留数量差异,力图建立起各种数学模型来表征世界,代表性成就是古希腊的行星天文学和阿基米德的静力学。第三种是实验的方式,是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的动手操作和精确观察。而17世纪科学革命的本质,正是这三种认识世界方式的相互融合。
这种融合是逐步完成的。举例来说,伽利略成功地把数学的认识方式和哲学的认识方式结合到了一起,所以他称自己是“数学家—哲学家”。波义尔则把哲学的认识方式与实验的认识方式结合到了一起,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实验哲学家”。牛顿最终完成了三种认识方式的综合。作为微积分的发明者、万有引力定律的创立者和牛顿环的演示者,牛顿将数学家、哲学家和实验家这三种角色完美地集于一身。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哲学认识世界的方式本身就内置在科学之中。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就好比数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这门学科本质上比较接近数学。哲学研究要遵循两条基本原则:首先要用清晰的概念来表达思想,其次任何思想都必须经过论证。这跟数学的要求如出一辙。除此之外,哲学跟数学都不仰仗于经验。对科学家而言,任何数学理论和哲学思想都只是他们用来理解自然的文化资源。哪种数学理论合适、哪派哲学思想能带来灵感,要服从自然或经验的裁决。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温伯格、霍金这样杰出的科学家会喊出“哲学对物理学无用”“哲学已死”的口号?
郝刘祥:当温伯格和霍金这样的杰出科学家“反哲学”时,实际上也暗自承诺了某种哲学立场。他们反哲学,多半是反形而上学,这实际上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主张。
逻辑经验主义是20世纪影响甚大的一个哲学流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是一服有效的思想解毒剂,能够帮助人们剔除芜杂的思想。海森堡创立矩阵力学、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都得益于实证主义这服解毒剂的功效。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逻辑经验主义是一种相当狭隘的科学哲学理论。
按20世纪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的看法,如果把科学知识比作一个圆盘,圆盘的边缘是人类的经验知识,从边缘往里是科学中的理论知识,圆盘的中央则是逻辑和形而上学。任何科学理论的内核都包含了形而上学,也就是该理论的本体论承诺。以牛顿力学和牛顿引力理论为例,它的本体论承诺包括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物质性微粒和微粒之间的超距相互作用力。
科学家的反哲学,某种程度上与哲学家的反科学是遥相呼应的。随着19、20世纪科学的分科化和专业化,哲学家很难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这使得许多哲学家选择了忽视科学甚至站在反科学的立场。比如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就反对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将科学知识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并一度引发了与科学家的论战。
《中国科学报》:大多数做科学研究的学者,对哲学既不了解也不关心。如何让他们相信哲学对科学的“有用性”,让科学家主动拥抱哲学?
郝刘祥:哲学对于科学的“功用”,可以分为一般和特殊两个方面。
从一般意义来说,哲学训练可以提升人们的思维严密性和思想高度。哲学是概念之学、论证之学,就此而言它有助于培养概念思维的严密性。哲学家关注的都是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此而言它有助于培养看待问题的宏观视野。人类是用概念之网来把握这个世界或实在的,这张网上重要节点处的概念,比如时间、空间、物质、心灵、规律、类、因果性、真理、美、正义等,都是哲学概念。这些基本概念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基础。
哲学的特殊“功用”,主要体现在哲学家通过对基本概念的持续关注而发展出的思想体系,往往成为科学中原创性思想的灵感之源。举例来说,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关于自然界数学化的思想,不仅激发了伽利略关于落体定律的研究,还激发了开普勒去寻找行星运动的第三定律。再比如,法拉第的场论思想,得益于力心原子概念;这一概念的历史渊源,则是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形而上学。
哲学的特殊“功用”,还体现在哲学家通过对科学认识论和科学进步的动力学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科学发展的“规律”,从而为科学政策的制定和科研体制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哲学的一般性功用,只能通过通识教育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哲学的特殊功用,实际上不需要上门兜售。按库恩的说法,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交替。在常规阶段,科学家完全有理由不关心哲学,因为他们的基本任务活动就是遵循范式的指引去解决难题。但在科学革命阶段,就会有科学家开始怀疑范式的适用性,这时他们就会主动跨入哲学的领地去寻找盟友。历史上的大科学家,莫不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爱因斯坦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所以我们总是称他们为“哲人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科学家的哲学自觉从何而来?国内能出现身兼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哲人科学家吗?
郝刘祥:科学家的哲学素养,显然来自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传承的文化。西方科学的源头之一,就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希腊人的哲学精神,深深地根植在西方的科学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抚慰心灵、安顿人生的哲学思想,但的确缺乏西方那种坚强有力的理性哲学传统。
中国要想培养未来的哲人科学家,需要加强理工科高等教育中的哲学通识课程建设,探索科学加哲学的联合教育模式,建立科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平台,营造有助于哲人科学家成长的文化氛围。培养未来的哲人科学家,正是哲学所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