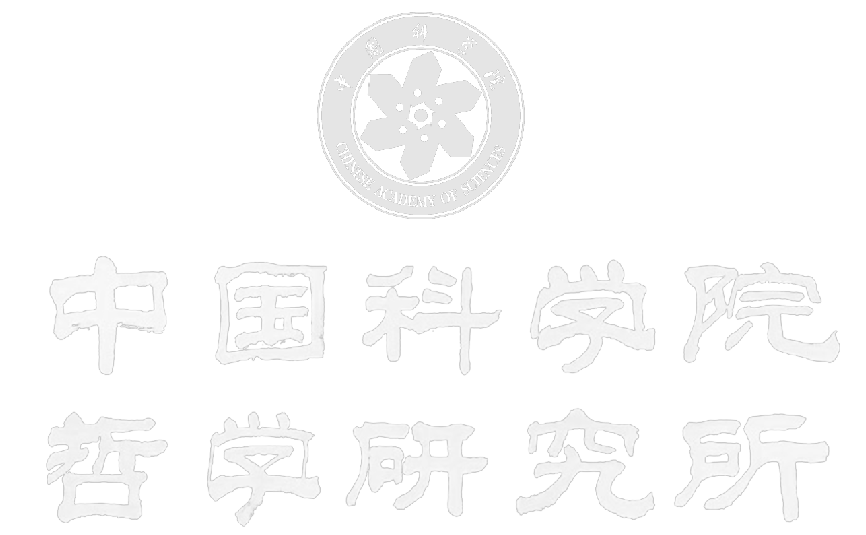.png)
引言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复旦大学智能科学与智能哲学研究中心将于9月15日与9月22日联合邀请纽约大学的迈克尔·斯特雷文斯(Michael Strevens)在线讲解他的新书《知识机器:非理性如何塑造科学》中提出的新的解释模型——这个模型试图解释近代科学如何从古代芜杂而多样的自然思考转变为近代科学不断创新与实证性的知识机器。本文将对斯特雷文斯的思想做出提要式的概括,以方便听众能够更加快速贴近他的关切。作者的初始关注点在于,为什么科学在当代变得如此强大,而强大的科学力量却竟然在人类文明史中非常晚近的时候才逐渐被人们重视,并成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以及近代科学的诞生与科学的不断进展果真基于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想与具有特定内部方法论特征的理论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作者认为需要追溯历史中科学转变的关键节点,寻找其中最为关键性原则。
如果回看古希腊或者欧洲以外的古代中国或古印度文明,这些文明的故地均产生了许多丰富的思想,科学的思想雏形或许也在其中,但是,这些科学思想的雏形却并没有像近代科学这样成为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活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按照斯特雷文斯的话说,这些科学思想的雏形,总是受到其他观念的影响,比如神学的或者美学的影响,使得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产生偏差。例如,有些古代的科学发现会将宇宙行星的运行秩序与上帝的统治秩序混为一谈,或者在解释自然的时候总是希望寻找对称的美感等。这些“科学之外”的思想,参杂在对于自然发现的“自然哲学”之中的时候,自然就成为了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
那么,为什么在近代欧洲发生了转变,使得朴素的科学思想转变成了今天人类通过系统而高效的“知识机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科学知识、并影响世界的呢?促成这个转变的重要“推手”是什么呢?斯特雷文斯带领读者回看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历史,试图说服我们相信这个“幕后推手”是科学的“铁律”(Iron Rule)。在斯特雷文斯看来,关于科学的“铁律”类似于一种关于知识的“法令”,它可以强有力地判定哪些知识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假说与科学知识),而那些不符合铁律的内容则应该被科学排除在外。我们不禁会问:这个塑造了近代科学与现代世界的铁律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科学铁律与培根趋同
在《知识机器》一书中,科学铁律被解释为将科学假说诉诸于实证检验的一种努力——即一切科学假说和理论的争议,都借助实证的证据做出终极判定,而且这个实证性的证据只能支持与解释对抗性假说争论中的一端。正如同一个法官不能同时支持原告与被告,科学铁律必须在知识法庭中,借助实验证据与数据对科学假说的真与假、合理与不合理、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做出公允和权威的判定。
与从前哲学家将实证主义作为科学准绳有所不同,在斯特雷文斯看来,铁律还是科学家追求真理的动机和源泉。他引用了科学家罗杰·吉耶曼(Roger Guillemin)与安德鲁·沙利(Andrew Schally)在竞争的案例。两位科学家同时试图在TRH荷尔蒙中寻找另一种微量存在的荷尔蒙LRF。为了证明这种微小的物质的存在,沙利不得不对16万头家畜的下丘脑进行处理,以此获得千分之一克的荷尔蒙提取物。科学家们为了通过铁律来追求科学知识的努力是他们自己往往并未自觉的,却成为了知识机器塑造科学知识的强大动力。
然而,科学的发现似乎也并不总是两种对立的模型或者假说的对抗性竞争,也存在着两种相近却存在差异的观点的互相辩论。与哲学或神学的辩论不同,斯特雷文斯看来,科学模型的辩论并不依赖文本与逻辑,或者美学与道德,而是借助铁律指导下不断收缩差异,逐渐趋同,逐渐形成相对统一的科学共识。这早在16世纪便被英国哲学家培根发现,一旦科学家开始使用他的发现方法来理解一种现象,他们会很快排除正确解释之外的所有解释。因而,在不同假说之间的趋同需要同样需要实验作为标准。后来,就连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一针见血地总结了培根之后科学观:“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的方法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和重要条件。”
“培根趋同”在科学史上有过许多例子。在本书中,作者提到,在1887年年,阿尔伯特·迈克耳逊(Albert Michelson)与爱德华·莫雷(Edward Morley)试图通过光学实验来验证当时关于宇宙介质“以太”存在的假说。然而,他们的实验却经历了痛苦的过程,由于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以太是宇宙普遍存在的介质,那么光在经过以太的时候,必然会有所变化,即使那个变化非常微弱。但是,他们的测量却始终沉浸在失败的情绪中,因为他们的实验数据始终不能与牛顿科学假说中的“以太作为普遍介质”的科学模型相容——直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证明了迈克耳逊与莫雷实验的准确性,同时推翻了“以太”存在的假说。
通过这些例子,斯特雷文斯说到,虽然亚里士多德与伊本·西拿等一种古代科学思想家有过伟大的发现和科学假说,但是由于缺乏铁律作为准绳,他们的思想要么参杂了关于宇宙秩序协律的美学考虑,要么要为神的存在做出留白,而他们的思想容易成为信徒们不容置疑的理由。而科学铁律的关键便是打破这些教条,将经验证据与实证分析作为唯一准绳。
科学体系与知识机器
读到这里,读者或许会怀疑,近代以来社会的巨大转变,现代性的种种似乎仅依靠铁律的标准与动力无法令我们相信它是塑造宏大知识机器的唯一原因。因为,理性地看,人类可能更容易将推理与理由作为理解科学的第一源泉,而从经验中汲取实证的力量却往往是非理性的,但却是铁律要求的。因而,斯特雷文斯得出了与以往科学哲学家相反的结论:科学铁律指导下的近代科学往往是非理性的、非效用性地选择了不断实验与求证的方法来推进科学发现,将科学与实验求证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单纯的理性推演。而在铁律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地是,铁律自身的公允,并不是因为某种独一无二的原则性,而是追求关于自然事实的客观性。
没有科学家们会相信自己所坚持和相信的理论是“不客观的”,但是,他们所坚持的这种客观却仍然存在某种局限。例如1906年的诺贝尔奖同时授予了圣地亚哥·卡哈尔(Santiago Cajal)与卡米洛·高尔基(Camillo Golgi),但是在颁奖典礼上,两个人却因为神经元是单一细胞还是网状结构而互相争辩起来。在他们看来,自己所坚信的才是最客观的科学发现,并具有自己的理由。在科学领域中这样的争辩似乎并不罕见。斯特雷文斯在解释这种现象的时候,他认为由于所有的科学家都相信解释力的重要性,而这种解释力通常在科学的公共领域中得到很好的展示。那么,这样一来,似乎最好的科学体系需要借助匿名评审的公开出版的科学刊物,对于同一问题进行细致和深入的互辩,并通过新的实验设计和发现来证明自己所坚信命题的准确性。
斯特雷文斯不止一次提到,对于由于科学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和多样性,铁律与铁律指挥下的科学体系所发挥的角色,类似于象棋规则。象棋的策略可以千万种,但是他们的规则是恒定不变的——在铁律与科学体系的作用下,新的知识机器就这样“诞生”,科学知识被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共同参与到这些知识的生产,并使之成为影响到生活与现代性的重要力量。
总结性回顾
斯特雷文斯在总结近代科学的形成的时候,除了关于铁律无意中被科学共同体“挑选”为讨论的标准外,也不忘讨论了科学产生的客观因素,那便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的欧洲,神学不再成为解释自然与世界的唯一源泉,世俗的政治体系与社会运作,使得民族国家将精力转移到商业竞争中,而欧洲大多数大学也在这个时候相继出现并走向非神学教育的正轨。
当我们再来回看《知识机器》这本书,不难发现地是,它为我们提供了解释科学产生与演变的另一种模式,那便是不再将科学诉诸于思想史内部的理性主义与感性思想斗争的结构性争论,更不需要诉诸于哲学、神学或者美与对称的考虑,而是通过辛苦地和大量重复地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观察与实验,并在其中总结出共有的特征或因果规律,并将这种特征与规律作为科学理论的重要基础与论据。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的欧洲,安定的政治环境激励了大学与科学发表制度的兴起,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科学讨论公共空间逐渐形成,进一步加速了科学铁律深入人心,最终成为科学家们从事研究的终极准绳与驱动力。科学铁律使得非科学知识与其他信念逐渐排除在了科学研究之外,使得科学发现回归到科学家共同体之中,使得知识的探索成为人类追求真理与客观性的纯粹活动。正如斯特雷文斯在本书结尾部分提到的那句:不要干预铁律。不要干预知识机器的工作。制定规则,然后退后一步;顺其自然吧。
作者
朱林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吴东颖(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



.jpg?x-oss-process=style/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