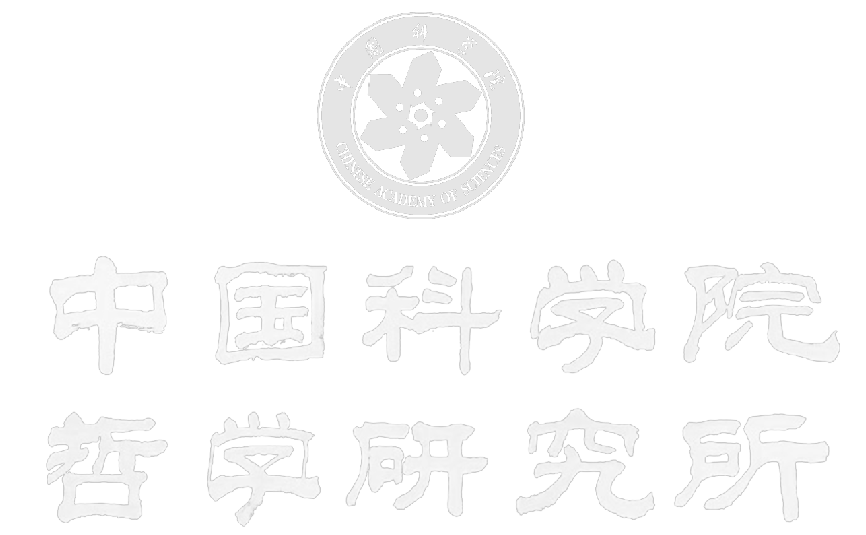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复旦大学智能科学与智能哲学研究中心于9月15日与9月22日联合邀请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2017年古根海姆基金会奖金获奖者、美国纽约大学哲学系中最有影响力学者之一的迈克尔·斯特雷文斯(Michael Strevens),在线讲解他的新书《知识机器:非理性如何塑造科学》。本文回顾9月22日讲题为“知识机器和科学中确证理论的角色”的讲座内容,共享哲学加科学之胜。
知识机器和科学中确证理论的角色
.jpg)
斯特雷文斯主讲内容
评论人与斯特雷文斯问答
两场讲座的线上回放:
知识机器与科学中的动机问题: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341127Gc
知识机器和科学中确证理论的角色: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q4y1o7MK



.jpg?x-oss-process=style/news)